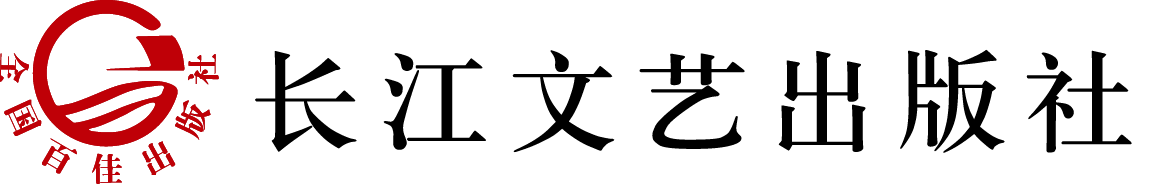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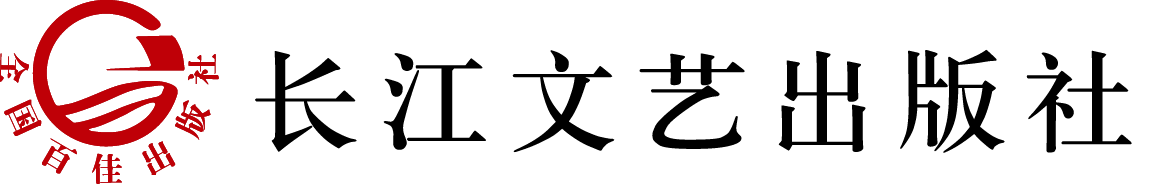
《你关不上大海》是著名散文家耿立的全新散文集,收录了耿立的一组书写大海的散文新作,如《你关不上大海》《海图》《鲸鱼的音乐》《去另一个美好的故乡》《一尾游向精神深处的鱼》等,部分篇目发表于《广州文艺》《青年文学》等刊物。这本散文集是耿立的散文转型之作,呈现出耿立散文创作的另一种风貌,在此前的乡村书写和历史书写之外,海洋书写为耿立的散文写作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全书围绕海洋展开,主题集中,文字流畅,具有较强的思辨色彩。
耿立,原名石耿立。中国作协会员。代表作有散文集《遮蔽与记忆》《向泥土敬礼》《灵魂背书》《暗夜里的灯盏烛光》等。《遮蔽与记忆》《向泥土敬礼》分别入围第五届、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曾获第六届“老舍文学奖”、第二届“三毛散文奖”、第三届“丰子恺散文奖”、百花文学奖等奖项。现居广东珠海。
一尾游向精神深处的鱼
一
秋风起了,官场到底也冷了,洛阳桥头的寒意,刺进骨缝里。
张翰的倦怠一日甚于一日,肚里的蛊惑馋虫也起了,吴中的莼菜鲈鱼,在这北地是没有的。
这是永宁元年(301年)秋。暮色中的洛阳官邸,张翰推开雕花木窗,吴郡同乡顾荣正烹煮新茶。秋风卷起案头公文,张翰突然按住顾荣执壶的手:“彦先,可闻见太湖水的腥气?”廊下枯叶沙沙响起,他解下腰间鱼形玉佩掷于案上,“明日我便要学这鲈鱼游回去”。
走,秋高季节,这时令正好鲈鱼脍。“人生贵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乎?”
归去来兮,回吴中去。
这是西晋版的《月亮和六便士》,张翰不想洛阳城里的六便士,他要看吴中家乡的月亮,莼菜与鲈鱼。
且说鲈鱼,乃海、淡水的洄游鱼,海里练筋骨经风浪,然后洄游到淡水的河里、湖里、江里,那张翰,也是一尾洄游的鲈鱼,一尾到月亮上的鱼。
这上面一段,是我几年前的文字,符合当时对官场与精神故乡,或者味觉乡愁的认识。但后来就觉得浅露,乃至鄙薄,这个诗意的表面背后,其实隐藏有很深的悲情和恐惧,生当乱世,只是借着一口故乡的鲈鱼与莼菜而湮没了。张翰的“莼鲈之思”不仅是乡愁,更是对乱世的疏离。乱世的知识分子命运,从嵇康“广陵散绝”的悲壮,阮籍“穷途之哭”的绝望,你就知道张翰以鲈鱼为借口的归隐智慧了。
如果现在让我重写,文章应该是这样开笔:
洛阳永宁二年(302年)秋。
暮色漫过官邸的鸱吻时,顾荣正用竹夹拨弄茶碾里的茶团。雕花木窗“吱呀”一声,秋风卷着枯槐叶扑上案头,落在了张翰公文的朱批上,像是一层霜。
“彦先可闻见太湖水的腥气?”张翰突然按住顾荣执壶的手。
顾荣抬眼望去,绯色官袍的友人立在窗边,衣袂翻飞竟似一尾挣扎的鲈鱼。
“季鹰又醉语了。”顾荣轻笑。
三更梆子撞破寂静。
张翰踩过满地撕碎的公文,“备车。”张翰想起二十年前,贺循的船泊在吴阊门外,他连鞋袜都未穿好就跳上船到洛阳来了。而此刻洛阳官道上的车辙却像无数条铁索,勒紧了他的神经。这时他也是未穿鞋袜,仍是光着脚,就踏上了返乡的牛车。
五更天。顾荣追到城门时,张翰的牛车已碾过最后一片宫墙的影子。
“季鹰当真要走?”
“彦先啊,”他掀开车帘,“你可还记得陆士衡的千里莼羹?”
张翰一天都不愿再在洛阳待下去了,他用一首《思吴江歌》与顾荣作别:
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
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一尾鱼,向着吴中洄游……
张翰辞官回家不久,大司马齐王冏谋反败露,被惠帝砍头,暴尸三日。其属官因牵连,也多死于非命,唯张翰在乡安然无事。
我思考着官场里的知识分子,怎样才能保持“文化洄游”的本能。张翰是清醒的,齐王司马冏掌权,征召张翰任大司马东曹掾。彼时时局动荡,张翰对顾荣喟叹:“天下纷乱如麻,劫难尚未见底。那些名震天下的人物,想要全身而退谈何容易。我本是山林野老,本就不合时宜。君当以明澈之智防患未然,以通达之思绸缪后路。”顾荣紧握其手含泪叹息:“他日定当与君共采南山蕨菜,同饮三江活水。”
鲈鱼洄游,这是自然的本能,但附加在鲈鱼身上的另一种东西,很多人习焉不察,这就是:鲈鱼政治学。我们还原一个场景: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铜雀宴。
一天,画舫行至漳水中央,油腻的庖厨小心翼翼呈上河豚脍。曹操青铜爵停在唇边,问:“诸君可知此宴缺何物乎?”杨修捧起错金博山炉:“丞相所念,当是松江四鳃鲈耳。”炉灰惊散,曹操大笑,将爵中美酒一饮而尽:“德祖聪慧过主,该赏鲈鱼刺身才是!”
曹操是个美食家,他写的《四时食制》就是他的家庭食谱,原书虽散佚,但人们今天还是能从《全三国文》《太平御览》《颜氏家训》里看到部分章节。曹操是吃鱼的行家,《搜神记》里记载了曹操的一件鲈鱼趣事。一次宴会上,曹操对着酒席,发出了叹息:“今日高会,珍馐美味,所少者,吴松江鲈鱼为脍。”方士左慈听后,便吩咐下人在铜盆注入清水,接着,就从铜盆中取出了两条鲜活的鲈鱼。曹操见此,接着说了句:“既得鲈,恨无蜀地生姜耳。”这时左慈再施神通,口中嘟囔几下。须臾之间,使者带回蜀姜。
曹操既耽于美食,更是政治运作的高手。鲈鱼在他的铜雀台成了一种政治叙事,风雅之物的松江四鳃鲈也成了为统治服务的道具,成了奖励的载体。听话就有鲈鱼吃,让主子高兴就有鲈鱼吃。古代中国可是把鱼作为待遇和礼遇的象征,“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食无鱼”,冯谖的牢骚家喻户晓,而柳亚子也曾学冯谖弹铗发牢骚,但最后这种撒娇被一顿政治安排,就马上转向“昆明池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
鱼成了一种政治境遇的砝码。在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境中,这种鱼的哲学是否在陶渊明的“望云惭高鸟”下感到脸红耳赤?
二
初客珠海,那是2013年3月,只身从鲁西南来,一副皮囊,手无寸铁,无相识之人,无可谈之友,天天囚在楼的顶层看云。看云从西江的入海口磨刀门那里激荡升起,虚空实在兼有,浓淡干湿,或白或灰,水气充沛,水墨的味道……那些日子,买了几刀宣纸,几本米芾的字帖,天天陪伴《苕溪诗帖》《蜀素帖》,老米的字也如云,裹藏、肥瘦、疏密、繁简。
刚离开故乡的不适,这时开始显现,首先是菜蔬面食,岭南的菜讲究本味,没有花椒茴香辣椒大葱芫荽,淡到极致;而米饭向来是我拒绝的选项。
胃袋开始感到不适,这时就思乡了,这思乡的蛊惑,多是幼年味蕾定势的诱导。吃不惯岭南本地的饭食,胃还是故乡的粮仓,储存故乡的芝麻豆花生红枣与小米。我的胃是节妇,只为故乡守着。彼时,还没遇到磨刀门下的鲈鱼,还不知磨刀门旁的白蕉镇的纵横河网池塘里,那咸淡水里有珠海的地理标志的海鲈鱼。
遇到什么物事都是讲机缘的,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
给不同的人开书单,虽书单不同,但《世说新语》是保留的,喜魏晋人物,无论嵇康、阮籍,还是小一号的阮籍——江东步兵张翰。这张翰,欧阳询也喜,有天下第七行书之称的《张翰帖》,就是欧阳询率更给张翰的礼物。这是欧阳询的致敬函,也是委屈的自白书:“张翰字季鹰,吴郡人。有清才,善属文,而纵任不拘,时人号之为江东步兵。后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纭,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执其手怆然,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鲈鱼,遂命驾而归。”这是欧阳询存世的四件墨迹之一,徽宗赵佶在墨迹后题跋一则,说《张翰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面折庭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徽宗只是从书法角度来说,晚年的欧阳询供奉朝廷战战兢兢,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欧阳询的家乡缺一尾张翰的鲈鱼,他是太子李建成的人,玄武门后时代,在李世民赐予的闲置里,他内心的苦和恐惧可知。
人们说欧阳询的字“险”,结体修长,中宫收紧,左敛右纵,化险为夷,有“骨”有“肉”,平正中见险绝。张怀瓘在《书断》称:“询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扰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笼之势,几旋雷激,操举若神。真行之书,出于太令,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
欧阳询字险,而他的人生也是处处险绝。欧阳询生当乱世,父亲谋反,满门抄斩,他侥幸逃脱。因其长相丑陋,李世民在一次宴会上让大家找乐时,欧阳询旁边的长孙无忌竟以欧阳询的长相作诗:“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角上,画此一猕猴。”这时的欧阳询已经是祖父级别的年纪了,在朝堂之上,还被人调笑。
如此,我们对欧阳询的《张翰帖》或者《季鹰帖》就会有深深的同情,那字里的精神向度,就不一般了。
喜书法翰墨,喜观帖寻碑刻,对书法里谈吃的文字尤感兴趣,特别是有鱼内容的字帖。
这就说到了怀素的法书《食鱼帖》:老僧在长沙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食肉,又为常流所笑,深为不便,故久病,不能多书,实疏。还报诸君,欲兴善之会,当得扶羸也。九日,怀素藏真白。
怀素这个和尚有意思,幼时出家,此时年华老去称“老僧”。在长沙时,老僧吃鱼,后北游长安,却没有鱼吃,那就只能吃肉了。和尚是要持戒的,老僧吃肉,难免被世俗耻笑,心里实在郁闷,终得日久生病。生了病,不能多写信件,确实疏于联络,所以要告诉朋友,若想集会,等我病好之后吧。
喜欢怀素病中的脆弱,这种弱,是需要抚慰的,像婴儿,像泪水,等待拭去,这种小小的病,只有展示给故乡和爱人的怀抱,他这是想家了,想长沙的鱼。黄裳先生说:“怀素是坦率的,他公开承认常常吃肉,白纸黑字,不怕被人抓住小辫子……”
读此帖的时候,真像看到了那一尾尾长沙的鱼,在长安市井深处,在泛黄麻笺上划过墨痕斑驳,向着馋嘴和尚说着不见老僧的苦恼。这哪里是清修比丘,分明是袈裟裹不住的饕餮老客。
《食鱼帖》的文字率性,让人看到了一个肉欲的贪嘴的酒肉和尚,这和法号里的“素”字,反差何止云泥,怀素一点都不“素”,也一点都不俗。怀素这个食鱼帖,不是创作,而是一个回复,或者便条,很随性,正如苏东坡所说:“其为人倜傥,本不求工,所以能工如此。如没人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近于有道者耶?今观此帖,有食鱼、食肉之语,盖倜傥者也。”
正因为随性,这正如张旭的《肚痛帖》,草圣腹痛如绞,偏要提笔疾书,墨迹似肠转千回。这与《食鱼帖》两帖并观,就见唐人笔墨里的烟火真趣,书法哪需要端着架子的庙堂气,市井悲欢亦可入墨,没有头巾气的人才可爱。
到了宋朝,东坡居士承此余韵,于黄州《寒食帖》中写尽人间悲欢。我对苏轼《寒食帖》更是熟知,犹喜东坡肥肥硕硕的字,对《寒食帖》的内容,是以平常的日记来看。也是苏轼被贬黄州的日子,东坡还贡献了《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豪放词和《赤壁赋》《后赤壁赋》,这些华美的文字留下,而墨迹没有留下,好在赵孟頫写有《赤壁赋》《后赤壁赋》,这墨迹在故宫,是书法与文辞的双美。必是鲈鱼,只有鲈鱼,才搅动了东坡。因为有了薄暮的举网得鱼,那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才惹得那锦绣文字做证,没有此鱼,何来后赤壁: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
鲈鱼乎,鲈鱼乎?鲈鱼也,鳞片助东坡之笔,秋风洗宿墨之砚。又是鲈鱼,这游上东坡墨池的鱼,一个浪花,就把《后赤壁赋》送上文学史。
设想,那年的秋天,有一尾鲈鱼游入了东坡的砚台。
元丰五年(1082年)的暮春,临皋亭竹梢缀满新雨,雨卷起几片枯叶扑在苏轼的窗棂上。他搁下笔,望着案头半干的墨迹,那是新写的《寒食二首》。纸间“空庖煮寒菜”的字句尚带着湿气,笔锋却是酣畅淋漓,姿媚、圆劲和沉着。
总得有人安慰这寂寞的东坡啊。
到了来年秋天,忽听得门外一阵笑语,两位布衣友人提着竹篓踏月而来,篓中一尾鲈鱼银鳞闪烁,鳃张如扇,竟将满室烛光搅碎成粼粼的月光和波影。
“子瞻!且看这松江之鲈!”友人掀开篓盖,鱼尾猛地一摆,溅起的水珠正落在苏东坡正读的《易经》第四十七卦:泽水困。苏轼抚掌大笑:“好个巨口细鳞!此鱼合该佐酒,助我续写赤壁风流耳!”
回到黄州第三载的寒食节,春雨淅沥。苏轼蜷在临皋亭的竹榻上,听着漏屋滴水敲打陶瓮的声响。案头冷灶几日未起烟火,唯剩半坛酸酒,几把老友徐君猷接济的糙米。他蘸着雨水研墨,在泛黄的宣纸上写下:“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笔锋初始时滞涩,似裹着江南潮湿的愁绪,写到“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时,枯笔突然在纸上划出凌厉的折痕,仿佛要将满腹郁愤刺破纸背。
苏轼贬谪黄州,恰似张翰故事的倒影。“自笑平生为口忙”的东坡居士,却在长江之畔日日与渔樵为伍,与麋鹿为邻,为一口饭而努力。某日薄暮,见渔人网中银鳞翻动,脱口便吟“桃花流水鳜鱼肥”,转念却怅然,此间非江南,鳜鱼亦非松江之鲈。直至十月十五夜,友人携来那尾“状似松江之鲈”的惊喜,才解了这文化基因里的乡愁。
是夜霜浓,东坡与二客踏着黄泥坂的落叶往赤壁去。江水在月光下泛着冷冽的青色,友人怀中的鲈鱼突然摆尾,打翻了酒具。清酒泼入江心,惊起潜蛟,也泼醒了苏轼的醉眼。“顾安所得酒乎”的叹息尚未落地,那尾挣扎的鲈鱼竟成了最妙的转机,取鱼烹鲜,折芦为杯,硬生生将一场缺酒少肴的夜游,酿成了“山鸣谷应,风起水涌”的天地大戏,绝妙华章。
赵孟頫后来重书《赤壁赋》,笔走龙蛇,处处可见银鳞闪烁。故宫的灯光下,观者总说那“举网得鱼”四字的连笔,像鲈鱼摆尾。想来松雪道人临帖时,必也闻见了数百年前长江畔的鱼腥与酒香。
黄州五年,苏轼发明了“净洗铛,少著水”的东坡肉,也琢磨出“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的奇思。但最堪玩味的,是他将寒食节的冷灶苦雨与鲈鱼宴的热烈并置,前者是“死灰吹不起”的沉郁,后者却是“俯仰人间今古”的旷达。这种苦中作乐的智慧,恰似他用鼠须笔写《寒食帖》:明明满纸萧索,却在“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的墨痕里,藏着对命运摇头的嘲笑,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即使在夜里,回家晚了,敲门不开,东坡也自有一种旷达,顺便听听江涛声: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每次读这首词,读到“江海寄余生”,就觉得东坡成了一尾鲈鱼,沿着长江洄游,曲曲折折,从黄州到白帝城,到渝州,然后转到眉州,回到上游的眉山故乡了。
某日东坡雪堂烹鱼,他特意拣出鱼骨置于案头,笑谓友人:“此鱼骨可作笔架,鳞片能研金墨。”后来《后赤壁赋》中“玄裳缟衣”的孤鹤,或许正是从这鱼骨笔架上腾空而起,驮着东坡的神思直上九霄,到琼楼玉宇悠哉一过。
风雅所钟,正在鲈鱼,后来明清文人案头,总爱置一盆松江鲈。文徵明画《赤壁图》,必要在舟尾逸笔草草,添几片银鳞;金农写札,自称“心似鲈鱼空自跃”。就连曹雪芹写大观园螃蟹宴,也要让宝钗笑道:“东坡云‘正是河豚欲上时’,我倒觉得该改作‘正是鲈鱼堪脍时’。”一尾鱼游过千年文脉,鳞片上竟沾满了墨香酒香书香和诗句的平仄,回乡的牛车与舟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