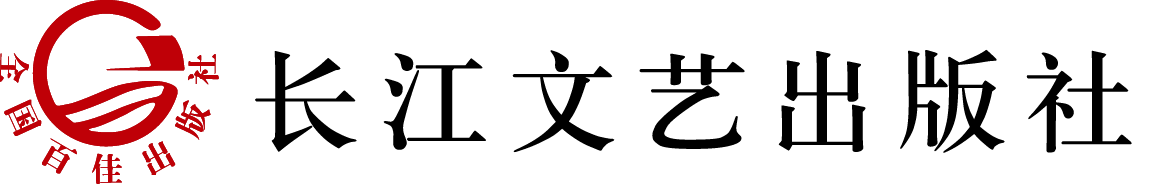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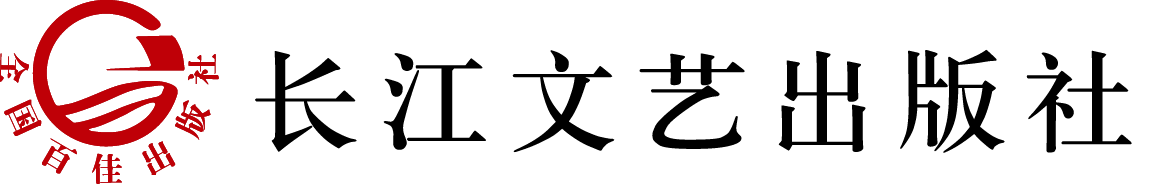
《夜巡》是上海新锐作家禹风的新长篇小说。 山乡青年驾牛一觉醒来,未婚妻吴三妹跟收山货的跑了,驾牛发疯般割了一草甸子的高草犹不解恨。表舅劝驾牛到大都市郊外的金鹤养老院当打杂工,驾牛来到了陌生世界:满院的老头老太婆都还精力旺盛,他们天天搞事,让当老人院总管的表舅头疼。 驾牛是不爱说话的“小哑巴”,女院长就需要他这样不起眼的“小乡巴佬”,她暗中交代驾牛当好院里的密探,尤其要关注夜里老人们都干些什么。驾牛就此成了养老院的夜巡人,他有山里练出的攀岩本事:一只“夜猴子”在养老院群楼外墙上攀附张望,好奇的眼睛打量着这个小天地被夜色掩藏已久的隐秘。 隐秘是不能随意打量的,驾牛身不由己掉进了漩涡,无助地看着老人院波澜叠起。 如果说女院长也是位老人,那么,其他老人们只能被看成老人院的经济作物。 连串意外汇成惊奇,真相仿如鲸鱼,缓缓浮出海面……
禹风,小说家,上海人,巴黎高等商学院硕士。著有长篇小说《静安1976》《蜀葵1987》《巴黎飞鱼》及《潜》等,作品发表于《当代》《花城》《十月》及《人民文学》等文学刊物,多描写巴黎、上海及北京的城市人生。
楔 子
跟进山收扁尖石鸡的老任跑掉的吴三妹,她本是我妈许我的女人。
吴三妹前一晚还孝敬我妈一篮子烤热的山芋,第二天一大早,她就跑了。
我表舅回村给他妈上坟,他一大早上的山,吃过山上老庙斋,下山正见我割草。唉,我当上金鹤养老会所护理工,其实是巧合,割草割出来的造化。
我本不想割那一大山坡草,可吴三妹和戴墨镜的老任据说穿过这片高草下的山,绕过了山门。
草高高旋着绿波,日头里漾起银芒,我忽就起了割草的心!
早先我做什么事都有节制。人家木楼上住家,楼下养猪,可我只养了三房间蜗牛。别人到农科站拜师,种三季稻,我宁愿在水田养田鸡;把水牛赶下溪,我骑上去,翻凉水下圆滑石头,找红背黑肚皮蝾螈。这些东西老任他们都收,不过给不了大价钱。
何必拼命挣钱?山里大多数男人打光棍,我既已订了吴三妹,一过门合着是两个劳力,为啥去拼一腔稀血?山里过活,蚊子蚂蟥都吃血,慢慢熬是正道。
我并没立刻下到大湖般草甸子里去。磨刀不误砍柴工,我拿出青石,蹚溪,舀一大桶彻骨寒水,坐家门口柳杉墩上,慢慢磨两把旧镰刀。
表舅那时正从山尖坟地上拜了下来。我两手食指和中指按住镰刀刀刃,嗤嗤嗤下力气。刀背红锈化几股细流。刃发了白,又泛青光,成一长条带凉气的银毫。
我把两把镰刀都搁背篓里,像篓子里养了两只活兽,听见它们铮铮地撕咬。我趴在溪边,脸浸没,浑身冒冰碴;张开嘴,溪水从喉咙灌下去,压不住心头火苗。
一脚踩进齐胸口的草甸子,草笼着腥,浪头那样打过来;绿溅到额头,顺风流回去,似女人摆腰肢,勾引我看那白芒尖。
吴三妹和老任早没了影子。正午烈日下,脚印已收干,土胀了回来。此刻我才梦里醒:一个谎话戳穿了!现在,我也成了摸不到女人边边一根山中棍。
表舅从山道上逛荡下来,恰见我舞开镰刀,像只疯猴子。
我没看见任何人。我想先学猿猴啸,喉咙只滑出一咕噜杂音。于是,我扭动起来,变成石蛙,跟草尖绿流打架,蹬着草茎跳跃,时不时弯倒腰杆。除去手里镰刀,我就是一只往死里折腾的蛙。表舅喊起来:“驾牛!驾牛!你发啥疯?”
如果我听见表舅的声音,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远行,就会窝在山里,眼不见为净。可惜我真没听到他!
我猛一下子低腰,真心开始割草,从草甸子边边开始,一直往东。镰刀根本没感觉任何牵扯,只见一大束一大团的绿在我眼前栽倒,甜甜的草腥腻得我喉头浮凸。
吴三妹,我割掉这草甸子,看你躲哪里?我割清光这草甸子,扯住老任,一把扒开他墨镜,看他到底多少岁?让我剃光这草甸子,叫草根上的油葫芦都藏不住身!让我一脚一脚踩死你们这些脑袋油光光的杂种!
表舅就是站在山路那黑石角上看傻眼的。他眼睁睁看我像一架联合牌收割机,标标准准、干干脆脆放倒了海一样的草甸;他看着我背上的天从青色晚成深红。
表舅后来告诉我妈说:“一只蚂蚁啃死了大象!一尾柳条鱼喝干了水库!看哪,这小子不是你养的,绝对不是你养得出的!割草甸子也罢了,别人越割越没力气,第一程割最长,歇着歇着,越割越短。这小子越歇,割越多,走越远,力气长得很!不会是个外星人?”
我没留意自己怎么割的草。我割草,为恨吴三妹。吴三妹应该是我老婆,竟跟狗日的老任跑了!
割草的时候,我心麻了,只顾看草唰唰往两头仆倒,猛然,吴三妹又跳进我眼眶,我心里疼,只好站住直起腰,等疼痛过去。
割着割着,我心头的痛一点点跟着青草倒掉,扯不住我了,所以越割越远。
等第二把镰刀刃口磨钝,吴三妹几乎随我的呼气跑干净了。
我用力扯住最后几捆青草,在草茎上磨刀口,甜甜草腥染我喉咙,我见血太阳落到西山巅,照得割倒的草甸子红灿灿,像大极了的打谷场。
表舅对我妈说:“让驾牛跟我走,山外头有钱,山外头有老婆!”
飞机飞到天上,没啥好怕;让人害怕的是起飞前那假模假式:你又不是只山猫,跑路前头也要扭屁股?好好爬着爬着,猛一停,肚子里发出呜呜声,震聋我耳朵!它这么个铁家伙撒开脚丫子就往前奔,我怕前头要有棵树,飞机都收不住脚。照它的架势,树得叫它扯出地来,带到云里头去!
没一会儿,它倒顺顺当当起来了,通身一抖,我看着候机楼沉下去,变成胡蜂窝。云在小窗户外头飘,我指头按玻璃上,心里轻松了。
刚有点开心,有个头顶上扣小布船的女人跑过来,抓流氓一样喊我:“老乡!你怎么把安全带松开了?快扣上!”
怎么了?这又不是裤带!
没飞多久,飞机冲着云下头的公路和小房子就扎下去。我看表舅,他闭目养神;再看跑来跑去送茶水的女人,她们自己跟自己在笑。我本就有点惊心,看见她们那种笑,心里更发毛了。飞机里很臭,没山的清香,人身上热气,夹杂纸头碗里撩起来那弯面条的怪味。耳朵疼得快让我听不见了。我看见飞机掉进了云,像打水桶掉井里。想对表舅喊一声,喉咙软得喊不出。要尿裤子了!咚一声,耳边响起嗡嗡的风……表舅睁开眼,看一看我,说:“飞机落地了。你比你表舅妈行!没尿!”
忘了怎么出机场,只记得身边到处是人,我像狗一样伸出舌头透气。
我没啥行李。表舅说过什么都不必带,养老院有的是!那里什么都比我用着的好。
不过我还是带上了我的狗皮袋子,这是大蛋的皮,它被黑熊坐了一屁股,死了。我扒下它皮,留着作纪念。
我搂着大蛋皮坐进接表舅的车。这车是来接表舅的,我只是件活行李,好比大蛋是死行李。开车的对表舅说:“黄老板天天问您几时回,快急疯了。”表舅笑着拍衣袖:“缺谁,地球照样转;嘴里没牙饭照吃!”
路上经过一个湖,表舅难得转过头对我开口:“看看!这是天底下最漂亮的湖——西湖!”
好一阵子,车像蜈蚣过草滩,穿过黑森森竹林,冲进一方青砖地,那里停了一排车。表舅对开车的说:“把行李推我房间去,我带小把戏吃东西。”
他拉拉我袖子,把大蛋的狗皮袋扯下来:“来!舅同你说话。”
他选了竹林一条窄路走,我跟到他后面,看他细瘦的身条子前倾着往绿荫里嵌。我盯住表舅的瘦屁股看,他坐得裤子遍是皱纹,皱纹大杈小枝,走路也甩荡不开。
表舅在小路到头亮光光的石凳上坐下,跷起二郎腿,对我说:“驾牛,知道为啥带你来城里?”
“啥?”我才不知道。
“不是因为我喜欢你,也不是光为给你妈捉钱;当然啰,也不会害你。”表舅看着我,一字一句说话,嘴角挂个冷笑。
“嗯。”我喉咙里应一下,不明白他说啥。
“叫你来,是因为养老院需要你,你也需要养老院!”他像山里人打牌,打到高兴处,把黑乎乎的底牌摊开。
我抓不住他的话,它们从他嘴里蹦出来,到达我耳朵前,却被风推开。反正,也不在乎他说啥。让我来,我就来。
“记住,你不爱说话,索性就当个哑巴!成了哑巴,你日子就好过多了。”表舅伸出手,手指又湿腻又冰凉,捏住我腮帮,像拍傻瓜那样拍拍我脸。
交代过这些话,表舅让我吃上了养老院的第一顿饭。
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我同桌吃饭。他叫食堂师傅弄一大碗热腾腾的米饭给我,然后又送来一个圆圆的银色盘子。每上一个菜,表舅先把他的筷子伸进去,夹出猪后腿肉、鸭腿、鱼丸子和鸡蛋,放我菜盘子里。
养老院吃得真好!我立马想到我会如愿以偿成为一个身上有肉的胖子。一种幸福感油然抹我心尖上:我有希望吃到肚子肉像锅水那样荡么?!
表舅立起来:“你吃相还好!给什么吃什么,也没把筷子伸出来。好吧,我直接带你去见见黄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