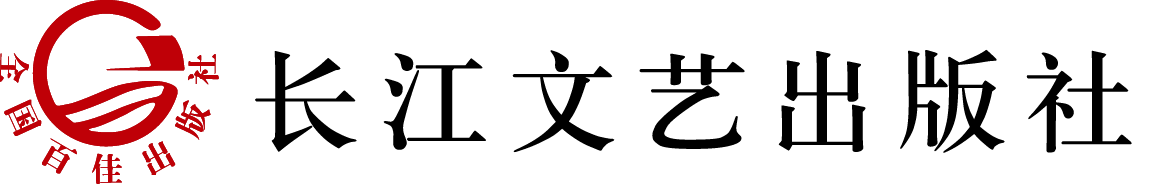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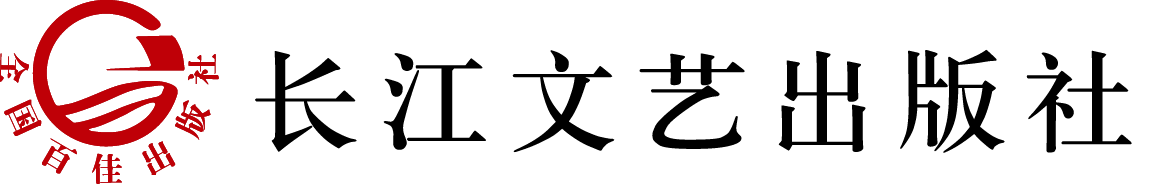
本书是关于古文物品赏和收藏的小故事合集。汉宝德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分享古物市场的变迁和个人的收藏趣事。 在汉宝德的眼中,古朴美重于一切:断了手臂的天王俑,在灯光的映照下,更显威严;残缺的石雕佛像,仍不掩“曹衣出水”的风姿;失去色彩的陶马、造型简单的宋砚,都有着静观可得的美感。 汉宝德娓娓道出古物收藏的深刻体验,不在意古物的市场价值,而侧重于对古物艺术之美的阐释,以及对古人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探讨。在真与假之间,辨证美的真实。
汉宝德,1934年生,台湾成功大学建筑学学士,美国哈佛大学建筑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学硕士。重要建筑作品包括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台南艺术大学、联合报系南园度假休闲中心等。
著有《如何欣赏建筑:汉宝德看建筑》《中国建筑文化讲座》《汉宝德亚洲建筑散步》《收藏的雅趣》《真与美的游戏》等。
破木板与旧瓦罐
话说我自一九六七年回东海教书并担任系主任,到一九七二年去美国教书一年后回国,住的一直是学校的宿舍,开始时“家徒四壁”,墙上没有挂任何东西。除简单的家具外,没有任何摆设。后来从美国的设计用品店里买了两张挂布,上面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流行的色彩鲜明的花纹,住处才有一点生气。在建筑系教书的庄喆兄与葛瑞福小姐分别借给我他们的作品,在东海的家里挂起来,家里遂有了既现代又传统的感觉,有点系主任家的气氛。
一九七三年回国前后,就在台北新辟的民生社区,买了一栋位于四楼的公寓,并加以改装,装成红砖与木板的室内。并建了壁炉,在餐厅的上方开了天窗,明显的是美国西部建筑的风格。这时候,光线最理想的餐厅的墙上挂的就是那张色彩鲜丽的花布。我自英国带回来不少铜版刻画的拓片,这时候派上了用场。我挂出来的,一张是在剑桥大学附近拓来的,十三世纪末楚平顿爵士的画像,一张是在伦敦近郊拓来的,十六世纪托玛斯·布伦勋爵的画像。这些拓片是我不远千里亲手拓来,自然十分宝贵。家里由此带来的一点古味却是古洋味。这时候,富锦街四楼的住宅后面的一个房间是我第二次回国后的工作室,我的学生张玫玫与登琨艳就是在这里帮我完成了天祥与澎湖的青年活动中心的图样。
这段时期也是我忙着修古迹与看古建筑的时期。由于传统民居建筑渐渐被拆除,市面上就出现了一种行业,把老建筑上的木雕与古物拆解出售。我并不很清楚这个行业是怎么开始的,以我推想,可能是美国人对民俗品的兴趣所引起的。在当时,国人正忙着除旧布新,上好的老房子都要动推土机清除了,哪在乎房子上的破木头?
当时在台湾的美国人很多,他们的眷属对于台湾本土的文物产生很高的兴趣,自老家具开始,逐渐发展到建筑的木雕,甚至宗教文物如木刻神像与神龛,有些接近他们的中国人乃动了做生意的念头,到处去搜购。
我的反应慢半拍。在四十几岁的年纪,我仍是现代主义者,满脑子的改革,对于把民俗文物当商品的行径是很看不起的。那几年我去了两次金门,看到了保存得比较好的金门传统建筑,更觉得建筑与民俗文物不可分割,因此没有一丝收藏的打算。可是风气是挡不住的,有一次在台中,朋友带我到一家店铺,店铺的后院子里堆满了各种大小的破木头,都是老房子上拆下来的,没有屋顶,风吹雨打,任其腐烂。问其主人,说可以随便挑。大约已经被台北的商人挑过了,实在没有好东西,可是又不忍心它们躺在露天的地上,就选了两块。记得每块是二百元。这是我买破木雕的开始,买回家来也是丢在一边而已。
一旦开始,瘾头就来了。这时候登琨艳为我做事,他的活动力强,常带些古怪东西回来。有一次他去彰化的一家年久失修的破庙买了一张大矮几,请木工修理好,抬到台北我家里。这个桌子木料并不好,但料大腿粗,有中国的古风,使我觉得是受日本影响的东西,然而矮几大到像张床,究竟做什么用呢?总之,这是我第一个老家具的收藏品,当时到我家的朋友无不惊异赞赏,还有古物商要我出让。这个矮几子摆在我家客厅里十几年,成为我家的商标之一,直到一九九五年先妻去世,要改装公寓内部,到了次年,我的儿子认为桌子不太合用,就捐给台南艺术学院了,至今尚摆在校长室的会客室里。
登琨艳还买了四只牛车的车轮子,当时我们对民艺品的古朴质拙,感到很大的兴趣,我就在客厅壁炉的前面放了一大一小的牛车轮。有一次一位美国友人到我家,说简直像到德州呢!后面因重新装修,这些车轮都分别送走了,我每翻到十几年前拍的照片,犹不免怀念呢!
一九七七年我转到中兴大学服务,离开东海,在生活上有很大的改变。一方面我要在台中弄一个住处,同时要对台北的公寓加以改造,以便尚滞留加州的妻子与两个孩子回来定居。在台中,我买了一栋公寓,同样在四楼,拜托建筑商按我的设计修改。在台北,则因建筑规范准许在顶楼加建三分之一的面积,就加建了大卧室,并在平台上做了花园,当局补贴了部分花木的费用。
我提到两所公寓的改建,与我的收藏兴趣有很大的关系,这时候我虽然还没有排斥外国装饰物,却已经喜欢用中国东西来点缀建筑空间了。我去中华商场的古物店买了两对建筑的雕饰,其中一对花鸟饰板装在床头上,一对金、红二色的龙纹雀替装在墙壁上。我已不再反对民俗品的商品化了。
学建筑的人大多喜欢陶器,因为自传统建筑上的砖瓦,到民间生活中的罐、瓮,距离是相当近的。鹿港有一堵墙就是用罐子砌起来的,罐子就用作建筑材料了。生活的器物中,以陶器最为普通,也最需要制作的技巧,它们是用陶匠的手,一个个地捏制出来,然后施釉,烧制而成,所以个个都是艺术品。文明民族的第一课就是陶器的制作,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发明了陶器,但陶器的造型与质感,却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比如中国民间的陶罐与瓷碗有共同的特色,与其他国家的产品有明显的差异。
我天生喜欢陶器,尤其是简单地上了点釉的硬陶,陶胎的质感加上粗釉烧结后的浓重深沉的色彩,很容易触动我。所以我在调查民居建筑的时候,偶尔在院子里看到缸、坛之类的大型器物,都会抚摸一下,却没有想到要买回家去。台北富锦街的屋顶花园做好后,我很想弄些瓦坛装饰一下,有一次凑巧去莺歌,路上经过一个制坛的工厂,满地摆了些烧坏的成品,不是歪头,就是斜体,我们情商主人卖了几个给我,我拿回家来,像宝贝样地放在院子里。可惜这些东西在后来修理的时候被工人扔掉了。
有了破罐子的因缘,我偶尔去士林一带的古物店走走,发现有一些来自大陆的陶罐。其中有圆体小口的黑釉罐,其表面粗糙,胎体凹凸不平,但釉光甚佳,上手后光滑又粗糙,令人爱不释手,很喜欢抱它一下。这类罐子种类不少,因无研究资料也不知来自何处、何时制作。只要看了好看,管它是台湾货还是大陆货,价格不过几百、几千,都买回家去,到处摆着,很快家里就成为杂货摊了。
我对陶器的兴趣不但广,而且大,有一次在北投一带的古物店里,看上一个日本式的火盆,颜色深蓝透紫,釉色很好,老板娘不肯卖,我们说好说歹,花了五千块买下。她送我们上车,还一直说我们lucky,好像挖到宝了。其实今天也不烧火了,要那么大一个盆子做什么?大火盆是吸引家人团聚的东西,所以表面打磨得很光滑,也不适合丢在院子里,只好放在卧室里,压缩我的活动空间。我家里已经到处是瓦罐,足证我已走火入魔了。
最后一次民艺品的收藏,是一个大缸。在乡下的宅子里偶尔看到这种八角形的缸,每边都有粗犷的图案,是闽南的产物,但可以转手的大都经台北的古物店转手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现今古物界名人徐政夫,当时尚未碰这些东西,约我陪他的老板蔡辰洲一行人去金门,准备赠送一座图书馆。到了那里住在山洞的招待所,晚上无事,我提议请军方派车送我们进城逛逛古物店。大家兴致高都跟着来了,在当地一位许老师的四合院里,看到他收的各种东西,也都有价码。在蔡老板的眼里便宜得不得了,就买了一大批雕得很细致的床头板回来送人。我先买了两件残缺的瓷件,及一个吊在屋檐下的小石狮,因东西小,容易携带。徐政夫劝我买大件,他负责为我运送。他说这话,我就买了院子里的一只大缸。他帮我运回台湾后,就放在屋顶的院子里。后来他为我在里面种了荷花,成为我家的一景。
震动后的天王俑
三月三十一日台北市来了一次五级地震,表面上看,与九二一的四级地震比较,波及似乎不大,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九二一之后,那么快又来一次大震!住在楼上的人免不了有些损失了,损失比较大的是收集瓶瓶罐罐装饰室内的人,我恰恰是其中之一。
我收集的是古物,种类很杂,对有钱人来说并不值钱,可是以我的收入来说,也不算便宜。我买古物喜欢买好看而且可供摆设者,买得多了难免要收起来,但家里的台子、柜子、桌子上还是摆了不少。由于我以古物装点室内,不太熟悉的朋友,尤其是外国朋友,来到我家都感到惊异。古物不是很贵重吗?你为什么这样不在意地随意置放?我只好笑而不答。
道理很简单,我的古物并不很贵重,而我买,是因为我喜欢看。我并无打算把它们视为投资或储蓄,买回家来,如不能常常欣赏到,其意义何在?在前文中说过,古物是玩物,是消耗品。为了能常欣赏到,必须经常摆出来,家里又不可能拥有如同博物馆那样的安全设备,自然免不了有损耗。这是在我计划之内的,因为这是必要的牺牲。我对于意外当然感到遗憾,却不会因噎废食。
这与图书馆管理的道理是相同的。图书馆,我向来主张开架式,而且尽量使读者方便。便利读者就容易丢书,若严格管理,虽不会丢书,却很少人来读书,两者相较,我宁采用丢书的宽松管理法,也不愿让书闲置而安全地封在书柜里。若无人读,要书何用?可惜图书馆的管理员不这样想。
言归正传,在过去若干年,由于我这样不经意地对待我的古物,曾有些损失是不待言的。损失比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工人到我家,不小心把一只明代的罐子打破,他不知是古物,还在街上选了一只更漂亮的赔我,我不得不向他千谢万谢。我总不能要他照古物赔吧!另一次是九二一地震,由于搬家,不知何人把一只南朝的青瓷大罐暂时放在高处,不用说,地震来了,把它摔成碎片。原本打算想法修理,却被用人当垃圾丢掉了。至于一些小的损失,诸如马被弄断腿,是可以轻易修好的,更不在话下了。可是有一次,一只北魏马车的轮子被摔碎,因为破成太多块,还是拜托朋友送到香港去修好的呢!
这次地震的损失,由于没有事先的防备,共有三件之多。有两匹马被摔是我想到的,在大地摇动的那一刻就知道了,因为我没来得及将其安放平稳。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一尊唐代的陶土天王。
唐墓中出土的随葬品,种类繁多,但数量最大的除了马与人物以外,就是天王俑。想来大人物过世,需要马队与侍从随行。在周代的古墓中,封建领主逝世,有大队车马与美女殉葬。后来儒家思想改变了这种野蛮的习惯,改以随葬品代替,中国人才进入文明社会。可是天王俑何以被用为随葬品呢?颇费思量。
由于地震之来,难以预料,而我又不愿把古物封藏保存,所以我不愿住高楼,能住地面最好,要住在楼上,最好不要超过五楼。否则一想到地震,岂不心惊肉跳?听说地震过后,每家古董店都有一袋袋的碎片待修,可见喜欢在家里摆出古物又住高楼的大有人在呢!
我推想这是中国自战国以来在墓中放置镇墓兽的传统演变而来的。古人为了安魂,在墓中放置驱邪的物品,在迷信的时代是很自然的。这个传统一直保持着,所以自汉到唐都有镇墓兽出土。早期的镇墓兽面目狰狞,形状也不悦目,以吓唬人的造形来吓鬼,到了唐代,一切都人性化了,唐三彩的镇墓兽虽然还是一脸凶相,整体看来却很讨人喜欢。早年我曾收藏过一个面目和善的三彩兽,简直是很可爱的样子,放在桌上也不觉得讨厌。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唐镇墓兽成对出现,一定是一个凶相,一个善相,最近我去柬埔寨访问了吴哥窟,才知道一凶一善是南来的传统,也就是佛教带来的印度传统。
我推想到唐代,佛教已很兴盛,佛寺中以天王为佛的护持是很流行的。其造像是威武的大将军,全身甲胄,脚下踩着鬼魅。称为天王,是对佛与菩萨的尊重,唐人可能认为它们就是驱邪的武士。既然墓葬中有驱邪的必要,天王应该比镇墓兽更有效力才对。所以在唐墓中,通常会出土一对镇墓兽,一对天王俑:是双料的驱鬼辟邪的保障吧!
对于收藏家来说,这两种东西,都为驱邪而设,不是很讨人喜欢的古物。他们比较喜欢美丽的妇女俑。如果勉强要收藏,镇墓兽是少人要的,天王俑因系中国后期武士造型的典范,还可以接受。可是我却认为唐天王俑可能是唐塑之中最有美感的东西。
唐墓出土的天王俑有各种大小与形状,并可大别为三彩与加彩两类。三彩类是上了低温釉的,色泽光亮,比较讨人喜欢,因为在当时是高级品,所以体型都比较大。加彩类是低温陶器,多是红陶,与砖瓦一样。表面加了白粉底,烧成后再在白底上画彩。这类陶俑价格低,所以各种尺寸都有。有不盈尺的,或是为小民准备的。但也有体型较大,彩色鲜丽,甚至贴金的。可见有些贵族宁喜欢手绘的、比较生动的加彩俑。三彩鲜丽,但不够写实。
我并不喜欢价昂的三彩天王俑。因为它们大多顾及了色彩,忽略了造型。艺术的价值不在光彩,在于面容与姿态是否有表现力。这是要比较才知道的。唐代的陶匠很多,天赋不同,作品的水准不一。他们是做了模子复制,复制的量似乎也不甚大。我见过很多不同形式的天王俑,以红陶俑中较有少数可观者。可惜红陶质甚软、脆,很容易折断,出土时不但色彩均随白粉脱落,身体也大多破碎。古物商之痛惜古物者,才会把断折的碎片收集,耐心加以黏合,使恢复造型的原貌,出土而保存原彩较多者就十分珍贵,虽然未必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看得多,没有真正满意的,本无意收藏。可是有一次在某古物店看到一对中型的天王,高两尺余,不论是比例、姿态、面貌,都使我动容。白粉掉了九成,只留下些微彩色的痕迹,有些肢体断失,可是整体的感觉却更显得富于雕塑美。细看,有些头饰是断过后接起来的,身体也有断痕,因为是低价品,修补时并未予以掩饰。问问价钱,就很不犹豫地搬回家了。
自此后,我家的天王俑就成为重要的陈列物了。在适当的灯光下,我真的认为不输任何过去所见过的唐武士塑像。在建设台南艺术学院的时候,其主建筑的大门显得单薄些,乃决定在门前建了一个简单的石坊,并加以雕凿,希望能增加些纪念性。门楣上刻了几个字,题为修艺进德之门,柱子上不知应雕些什么。思之再三,就决定把我家的这一对唐天王俑的上半部刻上去,也算求个吉祥。我把照片转交给上海美术院的工作室,塑出初模,再运到泉州去刻,如今是南艺的重要象征了。
三三一地震把我的一只天王俑震倒摔破,我免不了有些遗憾,但是把碎片捡起来,发现重要的部位,如面部没有摔烂,就算再遗憾仍抱一些希望。这座天王俑于出土时曾经历粉身碎骨之痛,是由某位细心商人修复,才来到我家里,如今在我家遭难,我希望考验自己的耐心,让我再一次地把它重建。第一次的劫难并没有使它减低多少美感,经我之手后,它会有另一种特殊的意义吧!
被震倒的这一只,是一对天王俑中比较完整的一只。我常想,另外一只少了一只臂膀,其实看上去比较孔武有力些。经过这次劫难,完整性大大减少,一些细致的尖角与凸出的装饰都不见了,这也许是使它呈现更勇武的面貌的一个机会吧。我究竟该为它惋惜呢,还是该为它庆幸呢?这也算是人生的一课吧